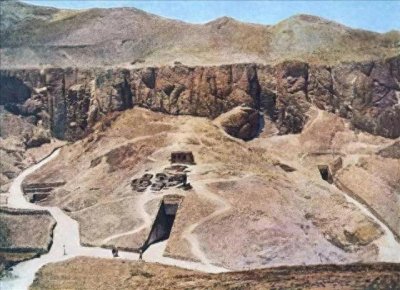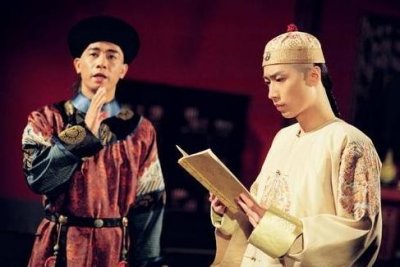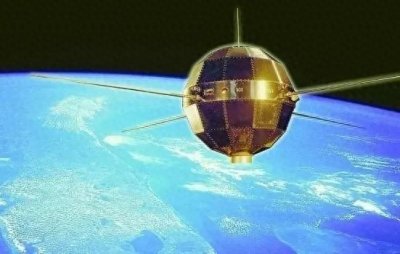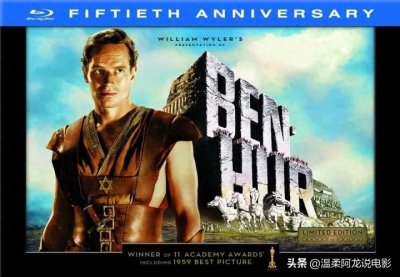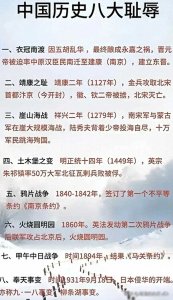明朝军户制度的血泪史:被历史遗忘的苦难群体
明朝军户制度的血泪史:被历史遗忘的苦难群体

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中,明朝军户的生存状态堪称历代军人群体中最为艰难的存在。这个特殊群体承载着王朝的军事使命,却在制度性压迫中走向集体性困境,其命运轨迹折射出明代军事体制的深层矛盾。
世袭枷锁下的制度性压迫
洪武三年(1370年)推行的户籍世袭制度,将全国人口划分为军、民、匠等职业户籍。军户群体自此陷入难以挣脱的世代枷锁,据《明史·兵志》记载,全国军户总数达160余万,占户籍总数的十分之一。他们被强制固定在边关要塞,既要承担军事任务,还需自备粮饷兵器,形成"平时为农,战时为兵"的特殊生存模式。
多重压榨下的生存困境
军户的经济负担远超其他户籍群体。正统元年(1436年)实录记载,大同镇军士需自备"盔甲、弓箭、腰刀各一件,锐钩枪各一杆",这些装备折银约需20两,相当于普通农户三年收入。永乐年间推行的"班军制"更令军户雪上加霜,轮班戍边的士卒需自行筹措往返路费,导致"鬻妻卖子,家业荡然"(《明宣宗实录》卷七十六)。
权力结构中的身份歧视
明代社会对军户的歧视形成系统性压迫。弘治年间《问刑条例》明确规定:"民户不得与军户通婚",这种制度性歧视导致军户群体社会地位持续下沉。正德年间南京守备太监的奏折显示,江浙地区军户逃籍率高达37%,逃亡者宁可沦为流民也不愿保留军籍。
军事体系内的残酷剥削
卫所制度异化为官僚集团的剥削工具。万历年间御史杨鹤巡视九边后奏称:"将官私役军士,多者三百,少者百余",这些被私役的军户既要承担将领私田的耕作,还要服侍其日常生活。天启三年(1623年)兵部档案显示,辽东前线军士实际领饷不足额定标准的四成。
末世困局中的集体崩溃
明末军户制度的崩溃呈现触目惊心的景象。崇祯二年(1629年)甘肃镇边军入卫京师,行军记录显示:"日行八十里,五日始得一食"。北京保卫战后,这些饿殍般的士兵返程时竟因"冲撞官轿"险遭问斩。这种极端压迫最终导致军户群体的大规模倒戈,据《流寇志》统计,崇祯年间前线部队哗变率高达63%。
当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会发现,明朝军户的集体性苦难绝非个人命运的不幸,而是军事制度结构性缺陷的必然结果。这个被历史遗忘的群体,用他们三百年的血泪史印证着一个真理:任何忽视基层权益的制度设计,终将动摇王朝统治的根基。
标签: